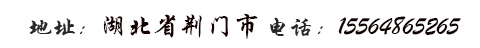译文远航者Voyager20
|
第二十章诊断 乔·阿伯纳西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两手握着一方小小白色卡片,皱着眉头。 “那是什么?”克莱尔招呼也没有打,走到他的桌边坐下。 “一张名片。”他把卡片递过去,脸上的表情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那是一张浅灰色亚光名片;十分高档,用花体字讲究地印刷着名字: 穆罕穆德·伊什梅尔·沙巴兹三世 下面是地址和电话号码。 “列尼?”她笑起来,“穆罕穆德·伊什梅尔·沙巴兹,还三世?” “呵呵,”好笑显然占了上风,他拿过了名片,口里的金牙闪烁了一下。“他说他不想再要白人名字了,他说那是奴隶的名字。他要重新宣布,自己是非洲裔。”带着一丝嘲讽,他接着说,“我说行吧;我还问他,你是不是还打算在鼻子上穿一根骨头啊?他不光要把头发蓄到这里”他比划了一下,“还要穿一个长到膝盖头的瓜子,看着就像他妹妹在家政课上做出来的瓜子。可不是,列尼——哦,对不起,穆罕穆德,他是铁了心要这么干了。” 乔朝窗外挥了挥手,指了指办公室外的花园美景。“我对他说,你四周看看,这周围还有狮子吗?这里是你以为的非洲吗?没用,这个年纪,说什么都听不进去。” “这倒是,为什么是‘三世’?” 他勉强笑了一下,“他这是要追寻自己逝去的祖先呢!他说,‘我去耶鲁上学的时候,怎么面对那些卡德瓦拉德四世、小休厄尔·洛奇呢?我连我祖父的名字都不知道,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从哪里来!’” 乔愁苦地哼了一声,“我告诉他,你想知道你从哪里来?你看看镜子就明白啦!反正你不是坐着‘五月花’号来的①!” 他又一次拿起名片,脸上带着一丝不情愿的笑容。 “所以他就说了,如果他要真的回归正统,为什么不全部回归呢?如果他的祖父没有给他一个姓氏,他就给自己的祖父一个。唯一的麻烦就是,”他拧着眉毛抬头看向克莱尔,“我被夹在了中间。现在,我只能变成老穆罕穆德·伊什梅尔·沙巴兹,这样列尼才能成为‘自豪的非洲裔美国人’。”他说罢倒回了椅子,下巴抵在胸口,一脸恶毒地看着那张浅灰色的名片。 “你真幸运,L.J.”他说,“至少布丽不会朝你哀痛自己的祖父是谁。你的烦恼也就是她会不会吸大麻,会不会和某个加拿大小子私奔而已。” 她大笑起来,声音也带着讽刺,“只你有这么想!” “啊?”他抬起眉毛带着一丝玩味看了看她,摘下了自己的金边眼镜,用领带慢慢擦拭着。“苏格兰怎么样?布丽喜不喜欢?” “她还在那里,找自己的历史呢。” 乔正要说话,一段敲门声打断了他们。 “阿伯纳西医生?”一个穿着马球衫的粗壮小伙子朝办公室探进一个头,胸前抱着一个巨大的纸盒。 “叫我伊什梅尔,”乔和蔼地回答。 “啥?”年轻人的嘴张了张,一脸凌乱地瞥了一眼一边的克莱尔,“那您是阿伯纳西医生了?” “哦不,”克莱尔回答,“这位就是,他脑子正常时就是啦。”她说罢站了起来,掸了掸自己的裙子,“我就不打扰你的约见了,乔,稍后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哦别,呆一会儿,L.J.”他打断了她,站起了身,从年轻人手里接过了盒子,正式地握了握对方的手。“您一定是汤姆森先生了?约翰·维克洛来电说你要过来。见到你很高兴。” “贺拉斯·汤姆森,是我,”年轻人眨了眨眼,“我……呃……带来了一具标本……”他朝盒子指了一下。 “是的,我知道。我很乐意帮您看看,不过我想兰道尔一声也可以给我做点协助。”他说着瞥了克莱尔一眼,眼角闪过一丝恶作剧。“我就是想看看你死人有什么本事,L.J.。” “你说什么本事——”克莱尔正要问,看到乔打开盒子,小心举起了一只骷髅。 “哦,很美,”他很欣喜地把那骷髅轻轻左右转动着。 “美”不是她脑子里想过的第一个形容词;这骷髅已经蚀迹斑斑而且褪色严重,骨骼已经变成了深褐色。乔把骷髅举到窗前透着光线观看,拇指轻轻摩挲骷髅上眼窝的边缘。 “很美的女士,”他轻轻说道,不知道是在对那骷髅还是对克莱尔或者贺拉斯·汤姆森。“成年女性,可能四十多岁、五十多岁。腿骨有吗?”他突然转身对那胖嘟嘟的年轻人说。 “哦,有的,在这里,”贺拉斯伸手到盒子里,“我们实际上有完整的骨骼。” 贺拉斯·汤姆森可能来自法医办公室,克莱尔暗想。有时候他们会把从乡间找到的严重腐坏的尸体送到乔这里来,请他从专家的角度判断一下死因。这具尸体显然是严重腐坏啦。 “来,兰道尔医生。”乔凑过来小心把骷髅递到克莱尔手中。“告诉我这位女士健康情况,我来看看她的腿骨。” “我?我又不是法医学家。”虽然这么说,克莱尔还是低头看过去。这不是一具古老的标本,也没有怎么风化;骨骼很平滑,带着新鲜标本所没有的光泽,是土壤让这骨骼染上了颜色。 “哦,好吧。”克莱尔轻轻在手中旋转着头骨,一边看着每一块骨骼,一边在心中默默念着它们的名字。颅顶骨光滑的弧线一直延伸到太阳穴,只指下颌肌肉的连接处。她生前一定有一对可爱的颧骨,高耸宽阔。上颌的牙齿几乎都健全——洁白挺直。 眼窝很深。可以看得出挖骨深陷;就算把头骨眼窝全部对着光线,也看不到完整的凹陷。头骨在她的手里感觉很轻,很脆弱。克莱尔摩挲着她的眉骨,慢慢一直到后枕骨,手指寻找着脑后的深洞——枕骨大孔,那里是所有的神经系统进入大脑的通路。 她又把头骨伏在在肚子上,闭上了眼睛,竟感到一种悲伤的颤抖,填满了凹穴,仿佛流水一般。她微微感到吃惊,那真是很古怪的感觉。 “她是被杀的,”克莱尔说,“她不想死。”她说罢睁开了眼睛,正看到贺拉斯·汤姆森正瞪着她,眼睛睁得圆圆的,一脸苍白。克莱尔小心翼翼把骷髅递还给他,“你们从哪里发现她的?”她问。 汤姆森先生和乔互相看了一眼,又看回她,两个人的眉毛都高高抬着。 “她是在一个加勒比海的洞穴里被发现的,”他说,“随着发现的还有很多艺术品。我们想她大约有一百五十到二百年历史了吧。” “什么?” 乔咧开嘴大笑起来。 “我们这位汤姆森朋友是哈佛大学的人类学系的,他的朋友维克洛认得我;让我能不能帮他看看这句人骨,告诉他我的发现。“ “该死!我以为你是让我看法医部门发掘的一个无名尸体呢!” “哦,她的身份的确是个未知数,”乔强调了一下。“而且看起来也很难获知身份啦。”他说罢开始像只猎狗一样在盒子里翻找。 “我们来看看还能发现点什么,”他一边说,一边拉出一只装着散乱的椎骨的塑料袋。 “哦,她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四零八落了,”贺拉斯解释道。 “哦,号,头骨连接着……颈骨,”乔轻轻说着,一块一块把椎骨排在书桌上,灵巧的手指码放着骨头,让它们排成一列,“颈骨再连着……椎骨……” “别理他,”克莱尔对贺拉斯说,“你越看他,他越来劲。” “好啦,现在,哦!”他惊喜地叫道,“上帝!L.J.!你简直神了!看!”克莱尔和贺拉斯·汤姆森依言都倾身看向椎骨上的一处尖锐痕迹。宽阔的脊柱轴心上有一道深深的凿痕;后关节突被干净利落地砍断,断裂面一直延伸到骨骼的中心。 “是脖子断了?”汤姆森好奇地看过来问。 “没错。我想还不止这些呢,”乔的一直手指在断裂面上慢慢挪动,“看到这里了吗?骨骼没有碎裂,就是从这里断开。显然是某人干净利索地砍断了这位女士的头颅。用的是一把钝刀,”他喜滋滋地做出了结论。 贺拉斯·汤姆斯看着克莱尔,不禁打了个冷战,“兰道尔医生,您怎么知道她是被杀死的?” 克莱尔脸红了起来,“我——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就是这么感觉到的,就这样。” “真的?”他眨了好几下眼睛,并没有追问下去,“真是好惊悚啊。” “她经常这样,”乔在一边说,一边用一把卡尺测量股骨。“不过一般都是对活人做推测就是了。总是能做出我见过的最棒的诊断。”他放下了卡尺,又拿起了一把塑料尺子,“你说是在一个洞穴里?” “我们觉得那应该是……呃……某种秘密的奴隶墓葬,”汤姆森解释道,有点脸红。克莱尔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一开始他在问哪一位是阿伯纳西医生时脸上的那份尴尬。乔尖锐的看了他一眼,只是低头继续着自己的工作,嘴里一边哼着《枯骨歌》一边测量骨盆内径,然后又是腿骨,这一次他注意力放在了胫骨上。最后,他直起了身,摇了摇头。 “不是奴隶,”他说。 贺拉斯眨了眨眼,“肯定是啊,”他说,“她周围发现的东西……肯定都是非洲的东西啊。” “不,”乔淡淡地回答,他拍了拍书桌上长长的股骨,手指轻轻敲打着干枯的骨头,“她不是黑人。” “你能从骨头看出来?”贺拉斯·汤姆斯显然有些激动,“我以为——根据延森的论文,我是说,关于人种的身体差异——”他的脸越来越红,有点说不下去。 “哦,是嘛,”乔干巴巴地说,“要是你觉得黑人和白人在皮肤之下没有不同,那随你的便吧,但科学上不是这么说的。”他转身拿过一本书《骨骼方差表》。 “你该看看这本书,”他邀请道,“你可以看到骨骼的差异,特别是腿骨。黑人的股骨-胫骨比例和白人的差别很大。这位女士,”他指了指书桌上的骨骼,“是白人。高加索人种,毫无疑问。” “哦,”贺拉斯·汤姆森嘟囔着,“好吧,我得说,太感谢您做的这一切了。额,谢谢你,”他有些别扭地微微点了点头。他们俩默默地看着他把骨骼重新放回盒子,走出了房间,在门口又朝他们张望了一下。 看着门终于关上,乔笑了一声,“要不要打个赌,他肯定还会把骨骼带给鲁特格尔,再问问他意见?” “搞学术的一般不会那么快放弃自己的理论,”克莱尔耸了耸肩,“我在这方面颇有感受啊。” 乔又嗤了一声,“显然啊!好吧,还是把汤姆森先生和他那位白人小姐撂在一边吧。说说,L.J.,你来找我有事?” 克莱尔深吸一口气,转身立定对着他。 “我需要一个来自一个可靠的人的,非常,非常诚实的观点。我只能指望你来帮这个忙了。” “没问题,观点。我能给。来吧。” “你觉得我是不是还吸引人?我是说从异性角度看。”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眯起了眼睛,自上而下地打量她。 “这问题很诡异,我要是回答不妥,是不是会给我扣上沙文帽子?” “不。”她认真回答,“我就是要听听沙文主义者的看法。” “好吧,那我就好好坦白……”他说着沿着她走了一圈,“皮肤很白,头发浓密,嗯,屁股很圆润。……波波也很美。”他又点了点点头,“满意了?” “嗯,我就是要这种回答。” 乔看着他,突然瞪着眼睛笑起来, “哇!简小姐,你遇到个男人啦!” 她觉得脸有点红,但还是得体地点了点头,“我也不确定,也许吧。” “也许!见了鬼了这是!老天爷啊,真该庆祝庆祝!L.J.!也该是时候啦!” “别这么吵吵嚷嚷的!”她说着做到书桌对面的椅子上,“他可没有你这年龄和身份。” “我这年龄?哇哦~~~~”他伸头问,“这么说他比你年轻喽?所以你有些担心?” “倒没有那么担心啦,”她感到脸上的红热渐渐褪了一些,“只不过,我有二十年没有见到他了。你是我唯一一个认得最久的朋友了;从你遇到我到现在,我是不是变化了很多?”她抬头殷殷看着他。 他也认真看着她,放下了手中的杯子, “没有,”他说,“你不会怎么变。除非你变胖。” “没有?” “没有。你这是要和高中同学重相会啊?” “我没上过高中。” “没有?不过我有过。我跟你说吧,L.J.;你要是看到一个二十年没有见的人,初见的第一眼,你会感到一点震动,心里会说,‘哦,上帝,他变了。’但是,几乎是立刻,这种感觉就会消失,就好像那二十年一下子没有了一样。我是说——”他眯着眼睛抬起头,认真思考着该如何描述,“你会看到头发有一些变化,也许有一些皱纹,也许和以前的穿着不一样了,但是经过最初两分钟的震惊以后,你会发现这些不同都不见了。他们还是你二十年前见到的那个人。你甚至得往后退上一步提醒自己,你不再是十八岁的那个你啦!” “但是,”他继续中肯地说,“如果人变胖了的话,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因为面貌会因为变胖而变得不太好辨认。”他说到这里,又扭头看着她,“但你不会,你不会变胖。这个就没在你的基因里。” “也许吧。”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她没有变胖。她手指还和以前一样,那戒指一直在原来的地方。 “是布丽的爸爸吧?”他轻轻问。 她猛地抬起头看着他,“你他妈怎么知道的?” 他微笑起来,“我认得布丽有多久啦?至少十年啦!她身上有不少你的影子,L.J.……但是我从来没在她身上看到弗兰克的模样。孩子父亲是红头发,对不?”他问到,“他肯定是个大个子混球,除非我读到的关于号基因的看法是假的。” “是,”她点了点头,突然感到一阵异样的温暖和兴奋。除了和布丽安娜和罗杰,她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和别人谈到过他。那种突然可以自由地谈论他的感受让她感到那样欣喜。 “是,他是个红头发的大个子,他是苏格兰人。”她的话让乔的眼睛又睁大了。 “此刻布丽还在苏格兰?” 她点了点头,“在她来的地方。” 两小时后,医院,留医院;把所有布丽安娜成年后应该需要的文件和证明托付给了乔。然后,她从停车场缓缓把车子开出,带着一丝惊慌,一丝抱憾,更多的是兴奋,踏上了自己的征程。 ①年,“五月花号”带着名清教徒从英国的普利茅斯出发在北美建立了第一块殖民地。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aluoteamaliya.com/amlygw/5393.html
- 上一篇文章: 不输普吉上海周边6大绝美海岛,假期必须
- 下一篇文章: 学讲话middot品典故交得其道